通过对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中的“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的深入探讨,我认为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重点在于突破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中国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对立,从而形成一种以未来为导向、重新诠释西方阐释学、承担世界阐释学使命的中国阐释学路径。这种构建并非简单地对三千年来中国已有的阐释经验进行形式化或理论化的整理,而是一种立足于古今交汇点,既区分古今又融合古今的创新性思路。
“中国阐释学”中的“中国”究竟该如何理解?它与西方阐释学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在探讨:在何种意义上阐释学可以体现出“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这一问题揭示了“当代中国阐释学”这一概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即后发现代化国家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时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普遍困境。正如张江教授所指出的:“目前我国的阐释学研究主要以西方阐释学,尤其是德国阐释学为核心,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长期主导着中国本土阐释学的研究方向,其概念、命题、范畴乃至方法已成为基本范式与准则,似乎离开了这些就无阐释学可言。”[①]要突破这一困境,就必须致力于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当代中国的阐释学为何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它与三千年传统中国阐释经验的关系如何?(这是当代中国阐释学构建中的“古今问题”,将在本文第三节详细探讨);其二,中国的阐释学到底是“阐释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阐释学”?(这是中国阐释学构建中的“中西问题”,本节将重点探讨)。
1930年6月26日金岳霖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撰写的审查报告中,[②]已经提出了“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之间的区分,这一区分在2004年中国哲学合法性之争中再次出现,并被视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层问题。中国阐释学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当我们提出“中国阐释学”时,中西问题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背景。“阐释学在中国”这一表述隐含着对普遍阐释学信念的认同:只存在普遍有效的阐释学,阐释学真理不可能受限于地域性或民族性。在此,“中国”仅是一个地理与民族的概念,阐释真理只是在此地被发现,但这并不影响其普遍性,因此“中国”也就无法成为“阐释学”的实质性限定词;而“中国阐释学”要想有意义,除非被理解为在中国发现的一般阐释学,这就导向了“阐释学在中国”。如果“中国阐释学”中的“中国”具有实质性内涵,那么它只能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阐释学。上述观点背后隐含的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相对峙的思想框架,且它预设了正确性只属于普遍主义一方,只要从普遍主义出发,“中国阐释学”要么失去自身意义,要么根本无法成立。
这种普遍主义的态度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从阐释学真理的有效性来看,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任何阐释学原理的应用都不应局限于特定的地域。然而,其盲点在于忽视了阐释学的风土性原则。阐释学真理是在阐释实践与经验中以运用的方式呈现的基本原则,它与一套在特定范围内被接受但无法被证明的“成见”相关联,这些成见由一系列的信念和假设构成,而这些信念和假设最终与具体的生活形式与文明传统紧密相连。阐释学真理的发现与承担主体并非形式化的纯粹理性主体,而是具有不同性情的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不同的风土环境中,语言、思维、历史、风俗、传统等因素最终融入风土性之中,形成个人得以自我确证的场域。与之相关,阐释经验与实践本质上无法脱离这种风土性背景。一旦考虑到世界性与风土性(地方性)的共同构成,那么所谓普遍性的一般阐释学本身也就无法与风土性相割裂,只有既基于风土性同时又能向不同风土的阐释经验和实践开放的阐释学,才被视为具有普遍性。即便如此,所有普遍性原则都有其特定的有效边界,正是由于这种边界及其有限性,才有了阐释学理论的更新换代。然而,人们往往将普遍性抽象化为可以从某一条最初原则——绝对的阿基米德点——推导出来的演绎系统,由此其普遍性是脱离经验的;然而,这种基于推理或演绎的普遍性仅限于形式普遍性,由于剥离了实质性内容,因而无法真正应用于阐释学实践,至少它将开放而具体的阐释学实践蜕变为现成原则的教条化套用。真正有效的普遍阐释学都植根于某种风土性的文明论背景,并能向更广阔的阐释实践开放,正是这种文明论背景赋予了阐释学以深度与厚度、丰富性与具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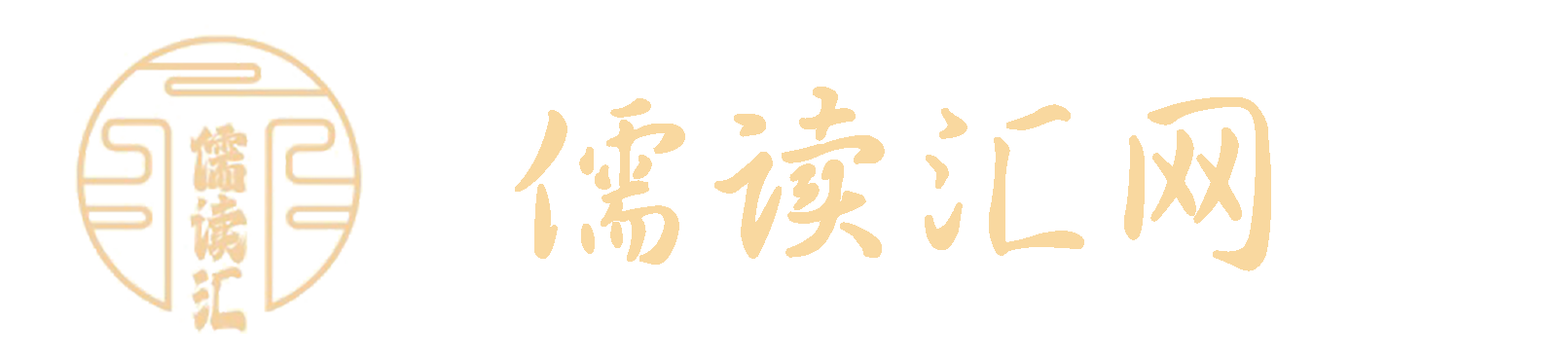 儒读汇
儒读汇